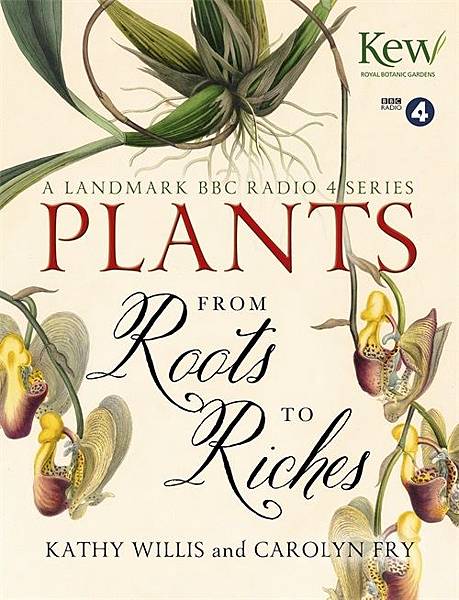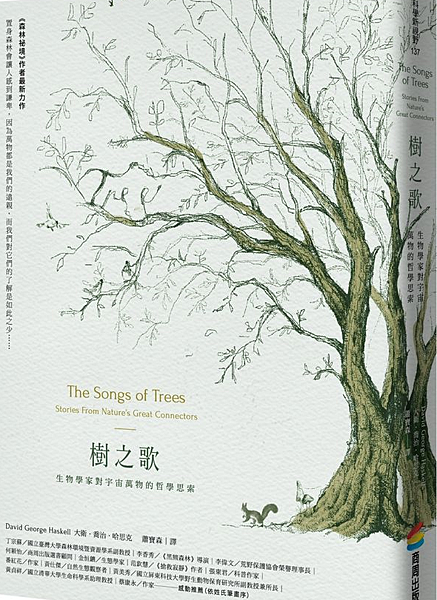英國皇家
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 ( II )

第4章
大地染上了晚疫病
BLIGHT ON THE LANDSCA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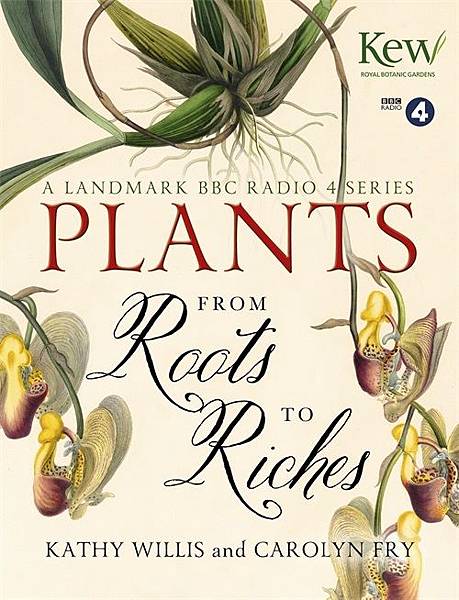

十九世紀晚期,試圖探索真菌各種不同作用的其中一位,是如今以她的兒童繪本而更為人知的科學家──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她繪製的真菌圖片非常詳細準確,而且她還涉足專業的真菌學領域。例如,她不僅會畫出子實體,也會畫出真菌生命週期中、於不同階段出現的所有型態。她也試著培養孢子發芽,並繪出了英國第一個關於單純銀耳(Tremella simplex)的記錄。
細緻地觀察真菌及其習性的結果,使波特開始對地衣深深著迷。對十九世紀的科學家來說,這些居住在地球上某些最極端環境裡的生物,仍是個謎。瑞士科學家西蒙‧施文德納(Simon Schwendener)擁護秋百瑞率先提出的想法,認為地衣是由真菌和藻類兩種不同的生物所構成,彼此維持一種寄生關係。在波特親身觀察後,她也開始相信施文德納是正確的。然而,和那時大多數科學界的女性一樣,她發現要讓學界認真看待她的看法是非常困難的。吉姆‧恩德斯比繼續這麼講述這個故事:「一八七四年,英國博物學家詹姆斯‧克榮比(James Crombie)曾譏諷,這整個關於地衣的想法就像是『被俘虜的藻類少女』和『暴君真菌主人』間不自然的結合一樣。事實是,碧雅翠絲‧波特這個名字已經和這古怪的理論畫上等號,這讓學界無法公平評判她的主張。」
波特熱忱地試圖找出地衣的真相。她在自家廚房裡培養藻類細胞和真菌孢子,觀察這兩個合作夥伴如何結合在一起,形成單一的有機體。要發表這類研究結果的最佳場所是林奈學會,但當時林奈學會並不接納女性會員。一八九七年,當她的研究終於能在林奈學會中發表時,卻必須由皇家植物園的真菌學家喬治‧馬西(George Massee)來代替她宣讀。在她的私人日記中,波特表現出對這位代言人的不屑:「我認為,在經過幾個階段的發育後,他自己也長成一株真菌了。」這篇經同儕審查的論文仍需進一步的修改,但波特從來沒將它完成。顯然,在這次經驗後,波特已對科學界感到幻滅,故轉而致力於兒童書寫,繪出她的幻想世界。

第15章
植物醫藥
BOTANICAL MEDICINE
英國科學家羅伯特‧羅賓森爵士(Sir Robert Robinson)是一九四七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這位知識巨擘的研究橫跨有機化學的各個領域,其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研發出如何以人工方式量產盤尼西林,也因此拯救無數生靈。不過,在他的諾貝爾得獎引文中更被加以強調的成就,則是「在生物學上極為重要的植物產物研究,特別是生物鹼(alkaloids)」。因此,什麼是生物鹼?為何它擁有如此高的價值呢?
生物鹼是植物產出的生化化合物當中的一類。雖然生物鹼的功能尚未被完全釐清,但它確實提供了植物本身一些保護作用,對抗病原菌與草食性生物。植物不像動物,遇到威脅時無法逃跑,因此得仰賴化學物質來保護自己。它們利用自身合成的化合物,也就是所謂的特殊或次級代謝產物(specialised or secondary metabolites)來對抗威脅。多數的生物鹼都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有苦澀味。苦澀味能驅走多數的草食性生物以及人類;然而,這些化合物也能為人類提供某些益處。它們通常能被當成藥物使用。
英國皇家植物園佐爾實驗室(Jodrell Laboratory)的副主任莫尼克‧西蒙茲(Monique Simmonds)博士研究植物產出的化合物成分,並分析它們不同的藥物潛能。「這些成分並非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存在,」她表示。「它們的存在目的,通常是為了保護植物本身,比如對抗昆蟲。」同時,有些成分則會使植物的葉片與莖幹上的細微小洞閉合,這與人類細胞調節發炎反應的過程類似,因此這些化合物可能具備了開發成抗風濕藥物的潛能。
現今使用的強效止痛劑嗎啡,是在一八○四年被發現的。它是最早被發掘的生物鹼之一,但分子結構卻遲至一九二五年才被羅賓森爵士解構出來。其他的生物鹼還包含可用來治療瘧疾的奎寧(quinine)及其後續衍生物,以及在馬達加斯加的長春花(Catharanthus roseus)中發現的化合物,它可用來治療兒童白血病與霍奇金氏病。
羅賓森最重要的突破是,他使用天然的原始材料與條件來合成這些強效複合物(以較簡易的材料產生化學反應並生產之),這個新方法與過去大相逕庭。以往是利用高溫、高壓的方法來製造所需的活性化合物。羅賓森的第一個成功例子是托品酮(tropinone),它被用來治療某些心臟症狀與支氣管問題,在進行眼科手術時也會使用。
藥用植物的歷史可追溯到很久以前。遠在科學家們開發出研究方法、來探討植物化合物及其獨特醫藥用途間的關聯性之前,人們就開始用它們來治療疾病了。以毛地黃(Digitalis purpurea)為例,外觀上它迷人的粉色、紫色鐘形花朵形象,和它實際所具有的毒性特質截然不符,這點可由它的暱稱「死人之鐘」窺見端倪。然而,它的治療功效卻是人類長久以來早已知曉的事實。一位英國醫師、同時也是植物學家威廉‧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他從古老的口傳知識中得到啟發,嘗試以毛地黃的浸液來治療水腫;該水腫是因體液淤積而引起的腿腫,經常與充血性心臟問題有關。他寫到:「在一七七五年,當我被徵詢一個治療水腫的家庭療方時,得知了在什羅普郡有位老婦人長久保存著這個密方。有時候一般醫生無法治療的病例,卻能被這位婦人成功治癒......這藥方包含了二十種以上的藥草,但深諳此道的人其實不難發現,這當中具療效的藥草就是毛地黃。」他將其拿來治療病患,成功率竟高達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但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晚期,毛地黃中的兩種主要複合物──長葉毛地黃苷(digoxin)以及毛地黃毒苷(digitoxin)才被分離出來,並被成功鑑定出這兩種活性化學物質具有調節心臟運作的功能。

柳樹皮被視為草藥,這樣的紀錄在官方史料上極少出現;它被發現具醫藥特性的過程,純粹是機緣。一位英國牧師愛德華‧斯通(Edward Stone)記載:「過往的經驗讓我發現,有一種英國樹木,它的樹皮是強效的收斂劑,對於治療瘧疾﹝熱病﹞與間歇性的疾病極具療效。大約六年前(一七五八年),我無意間嚐了它一下,它極端的苦澀味太讓人驚訝了;但同時也讓我猜想到,它可能擁有祕魯金雞納樹皮(cinchona bark)的特性。」斯通為此收集了一些柳樹皮,將它們乾燥後磨成粉末,並在他家附近的牛津郡鄉間地區對村民進行試驗。他將試驗結果發表於當時權威的科學雜誌《自然科學會報》(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隨著對柳樹的興趣日益升高,一八二八年,一種名為柳醇(salicin)的化合物被證實是柳樹所具有的活性成分。它在實驗室中可轉化為水楊酸(salicylic acid),是一種強效的解痛劑,但也與引發胃痛和胃潰瘍有關。一八九九年,德國科學家將水楊酸化為乙醯柳酸(acetylsalicylic acid),對胃部較無副作用。這就是現在所熟知的阿斯匹靈。
罌粟(Papaver somniferum)的醫療效果,和它細緻美感的鮮豔花朵及獨特的圓果外殼一樣,長久以來都備受讚賞。鴉片就是從罌粟的乳白色汁液中萃取出來的。希臘與羅馬時期的史料記載,罌粟是一種能紓解悲傷與減輕痛苦的藥物;而文藝復興時期的藥草學家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則相信罌粟能使人永生。到了十九世紀,當時的中國強烈反對英國傾銷印度鴉片進入中國市場,因此鴉片成了兩次戰爭衝突中的要角。罌粟所含有的主要活性化學成分,就是首個被分離出來的生物鹼──嗎啡。嗎啡在一八○三年被成功分離,一八二七年被命名,並開始在德國進行商業量產。

當然,皇家植物園也注意到了生物鹼的藥用益處。十八世紀晚期開始至今,世界各地的藥用植物都陸續落腳英國皇家植物園,被培植、研究,並分送至其他植物園。而自一八四○年起,英國皇家植物園與英國皇家藥學會也開始收集生藥,如磨成粉末的樹皮、切成塊狀的根、乾燥的葉片,以及無數的藥材。如今,皇家植物園的經濟植物典藏中心(Economic Botany Collection)大約存有兩萬份的樣本。在光潔木櫃內的收藏,見證了那個年代裡無畏的植物獵人、先驅的藥理學家、以及早期製藥者們的努力成果──在那個有至少四分之三的藥物都是從植物中萃取出來的年代。近來典藏中心增加的收藏,還包括了過去二十年間自中國收集而來、將近四千種的藥草,反映出全世界醫藥與醫藥系統的持續進展。
這些皇家植物園的木櫃,是十九世紀下半期藥師們的醫藥訓練箱。木櫃裡的藥材提供了藥師絕佳的機會,可以提早認識大量的藥用植物;這些藥草被認為可以治療維多利亞時期的各種疾病。在當時,人們對七大罪中的暴食似乎不太在意,因此有許多疾病都與消化不良有關。治療的瀉藥中包含了番瀉葉(senna),亞洲大黃(Asiatic rhubarb,與英國植物園的品種不同),以及蘆薈。蘆薈的黑色乳汁之功效,與現在拿來舒緩用的蘆薈凝膠,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櫟癭(oak galls)則被認為能有效治療腹瀉。
在經濟植物典藏中心(EBC),可以找到更多維多利亞時期的療方,治療更嚴重的健康問題。比如鴉片產品,像鴉片酒就是頗受歡迎的止痛劑,上至維多利亞女王、下至嬰兒都會使用,女王就曾在分娩時使用過。烏頭(Aconitum napellus),是莎士比亞劇作裡家喻戶曉的角色──羅密歐用來自殺的毒藥。加入烏頭的溶液,是當時廣泛用來治療熱病及所謂「汗症」的療方。治療熱病在當時是極其重要的事,因為不僅大英帝國在不斷擴張的世界各領地內有著嚴重熱病,就連自家門口也備受威脅。每年夏季,倫敦、肯特郡、諾福克郡與林肯郡的沼澤地區皆有熱病流行,而這熱病就是我們熟知的瘧疾(malaria,後來被稱為agues)造成的。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年少時就曾得到熱病,並終其一生深受反覆發作的痛苦所折磨。當時認為這些病症是「壞空氣」造成的,此即malaria一詞的由來。

藥用植物發展史與皇家植物園兩者最精彩的交集,就是抵抗瘧疾這點了。經濟植物典藏中心(EBC)的收藏品中,有超過一千種的樣本都與金雞納(cinchona)的發展及用途相關。金雞納樹的樹皮擁有療效,它內含奎寧及各種衍生物,可以對抗引發瘧疾的瘧原蟲(Plasmodium parasites)。據說金雞納樹是以西班牙金瓊(Chinchón)伯爵夫人來命名;傳聞在一六三八年時,就是該樹皮治療了染上熱病的伯爵夫人。而當時熟知這帖自然療方的耶穌會傳教團,則將其稱為「金雞納」(quinquina)或「樹皮之王」。
包括大英帝國在內,對那些有染指熱帶地區野心的歐洲帝國主義者來說,瘧疾真的是一種災難。數以千計的生命在非洲與亞洲的擴張征戰中喪生。在十九世紀一位英國船員的詩歌疊句中,這段歷史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被巧妙總結出來:「要小心注意那貝南灣啊/四十個人去了只得一人返。」如今,前線迫切需要對抗瘧疾的療方,因此尋找金雞納樹皮抵抗瘧疾的任務刻不容緩;但找尋收集金雞納樹皮的工作卻面臨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它的原生地分布於安地斯山脈一些最不易到達的地區; 另一個問題是,金雞納樹約有三十種物種,但沒有人知道是否所有種類、或當中只有某些種類的樹皮才擁有神奇的力量。

金雞納樹
為了帶回金雞納樹的樹皮及種子,數十個探險隊整裝出發,但大半都鎩羽而歸,許多採集者都被叢林給吞噬了。十八世紀時,法國的拓荒者拉孔達明(Cha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他也使我們注意到產生橡膠的樹種)設法尋得了正確的金雞納樹皮與種子並準備運往歐洲,但它們卻隨著沈船沒入了大海之中。就如同馬克‧宏尼斯保(Mark Honigsbaum)的著作《熱病之路》(The fever trail)中寫的:「這樹似乎像是被古老的印地安詛咒所保護著。」
金雞納樹與種子最終還是成功地運抵了歐洲。一八二○年,法國的化學家皮埃爾‧約瑟夫‧佩爾蒂埃(Pierre Joseph Pelletier)與約瑟夫‧凱文區(Joseph Caventou)首次在實驗室中將奎寧從金雞納樹皮中分離出來,不久之後佩爾蒂埃便在巴黎建立了奎寧萃取廠。在這重要的新藥探索爭逐賽中,英國也不甘落於人後。一八二三年,霍華德氏藥廠(Howards & Sons)也開始生產奎寧生物鹼。霍華德氏家族企業的一位後裔約翰‧艾略特‧霍華德(John Eliot Howard),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受矚目的奎寧專家之一。他同時身兼植物學與化學的專業背景,為他在辨別倫敦碼頭上一袋又一袋的金雞納樹皮時帶來莫大助益。在倫敦家中的溫室,他也致力於種植不同種類的金雞納樹,更是增長其專業知識。約三十種的金雞納樹彼此相似,容易雜交,而每種樹皮都有著各自不同的藥用生物鹼圖譜;雖然如此複雜,但霍華德總是能夠找出其中最有效的種類。

然而當時的夢想,是希望能在大英帝國所控制的領土內廣泛種植金雞納樹,並大量生產優質低價的奎寧。由於當時英屬印度的瘧疾致死率相當高,想當然耳,印度當局自是極力推行這項計畫。此計畫由英國皇家植物園規劃,他們組織了一個英國團隊,於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年間啟程航向南美洲。理查德‧斯普魯斯(Richard Spruce)與他的植物學家同僚們收集了種子與植株,帶回皇家植物園,並將它們寄送到印度。那些在艱困旅程中存活下來的、並在之後也被證明能產出奎寧的植株,便在大吉嶺山丘地與南印度等地廣泛栽種。隨後在一八六○年代,醫療官員們在馬德拉斯(Madras,即現今的清奈)、孟買(Bombay)與加爾各答(Calcutta)等地進行大規模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將移植印度的樹種樹皮中萃取的四種奎寧生物鹼合併使用,對於治療瘧疾有很好的效果。隨後,印度當局更利用龐大的郵政系統來廣發奎寧,以確保即使是偏鄉地區最貧窮的人民,也將能取得奎寧來治療瘧疾。
相反地,也有著與英屬印度截然不同的例子。當時,在荷蘭的殖民地爪哇種植了一種特殊的金雞納樹品種,該品種含有豐富的主型態奎寧生物鹼,在歐洲藥典中備受青睞。爪哇靠它締造了豐盛的外銷產業。查爾斯‧萊傑(Charles Ledger)隨後也到玻利維亞收集了該品種的種子,當然他少不了在地嚮導的陪伴,如果採集過程中沒有在地嚮導的陪伴,這些歐洲的植物採集者沒有一個能生還,更別提要找到目標植物,或理解其用途了。萊傑的嚮導是曼努‧音夸‧馬瑪尼(Manuel Incra Mamani,這位在地嚮導的名字能為世人知曉,這例子實在很罕見)。但可惜的是,萊傑與馬瑪尼都沒能在這項尋覓種子的功績中獲益。一八六五年,當收集到的種子抵達倫敦時,印度的金雞納樹培植事業已經相當成熟,因此皇家植物園對這批種子興致缺缺。最後,這批種子僅以六百荷蘭盾(相當一百二十英鎊)賣給荷蘭,馬瑪尼則因走私種子被逮捕,數年後就去世了。
因為歐洲對金雞納的需求,使得金雞納樹被大量砍伐剝取樹皮,到了一八五○年代,原生地安地斯山脈的金雞納樹量幾乎已瀕臨耗盡。還好,荷蘭與英國及時在他們的亞洲殖民地種植了金雞納樹。
一九三○年代,研究人員將奎寧化成氯化奎寧(chloroquine)與伯氨喹(primaquine),這是最早被合成出來的兩種奎寧衍生物,且都是有效的抗瘧藥劑。但隨著對這些療方所產生的抗藥性越來越高,新藥的研發也跟著驅動。一九九○年代,持續進行的新藥研發達到了巔峰,當時發現一種相當有潛能的抗瘧劑 ──青蒿素(arteminisin),它是從黃花蒿(Artemisia annua)分離出來的生物鹼,其原生地在亞洲的熱帶地區。
能夠發掘青蒿素,得歸功於傳統中國醫學的啟發,傳統中醫就有用來治療熱病的藥草。古老與現代的傳統知識相繼提供重要的線索給研究者,來辨識這類藥草。估計資料顯示,世界上已知的植物種類當中,大約只有百分之二十被研究、開發其藥用潛能;在這種時候,這些線索的重要性就顯而易見了。
即使如此,在所有的藥物當中,就有約四分之一來自植物或真菌產出的化合物;從後者開發出來的藥物中,就包含了抗生素、免疫抑制劑、治療高膽固醇的藥物,以及抗癌藥物。皇家植物園正在進行研發的,是可被用來治療輕微至中度阿茲海默症的加蘭他敏(Galantamine);另外與萊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共同合作的實驗則證實了,從稻米分離出來的麥黃銅(tricin)具有治療乳癌的潛能。
皇家植物園的研究人員站在研究的最前線,帶領我們更進一步地了解植物所含有的化合物圖譜,這些知識能夠解釋藥用植物在傳統上的用途。「皇家植物園已經是公認最值得信賴的單位,」實驗室副主任西蒙茲表示。「我們每年有超過一千項的諮詢,希望能協助鑑定藥用植物。這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植物在鑑定後,發現根本不符合其原先所聲稱的藥物、化妝品或食品用途。有時候是因為植株不正確,或是取錯了萃取液。我們最常被請求鑑定的物種,就是人蔘。我們得檢查在市場上販售的人蔘是來自美洲還是亞洲的品種,因為美洲品種是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所保護的;這也是皇家植物園在動植物保育上應負的責任。此外,我們也會檢查送檢樣品是否有毒性物質存在。」

皇家植物園的藥劑師梅拉妮‧豪斯(Melanie Howes)致力於研發治療失智症的藥物,她由睡茄(Withania)著手進行研究。這種原生於印度的美麗植物有著天鵝絨般的葉子,及包裹深橘色莓果的紙質外鞘,通常被稱為印度人蔘(Ashwagandha、Indian ginseng,也稱冬櫻花),它的名稱恰好顯示了其在醫用潛能上的重要性。在悠久的古印度阿育吠陀醫學中,印度人蔘一直是抗疲勞、疼痛與壓力的補品。

睡茄,印度人蔘。經研究認為,其生化特性有對抗失智、痛風、糖尿病及癌症的潛能
皇家植物園的藥劑師梅拉妮‧豪斯(Melanie Howes)致力於研發治療失智症的藥物,她由睡茄(Withania)著手進行研究。這種原生於印度的美麗植物有著天鵝絨般的葉子,及包裹深橘色莓果的紙質外鞘,通常被稱為印度人蔘(Ashwagandha、Indian ginseng,也稱冬櫻花),它的名稱恰好顯示了其在醫用潛能上的重要性。在悠久的古印度阿育吠陀醫學中,印度人蔘一直是抗疲勞、疼痛與壓力的補品。
豪斯與紐卡索大學合作研究印度人蔘的根部萃取物;經過測試之後,發現萃取物中的物質對導致失智症的兩種認知型障礙有阻抗效用。而其他研究單位也對印度人蔘的其他生化物質進行分析研究,以期能應用於治療痛風、糖尿病與癌症上。
先進的高端技術,伴隨著來自傳統藥草知識的民俗醫療指引,使得科學家篩選潛在藥物的工作如虎添翼。以DNA為基礎的研究,讓植物學家們能更加清楚地瞭解植物種類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幫助他們找出具有類似生化特性的植物,進而篩選出有藥用潛能的物種。
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是一塊吸引科學家從事研究的磁石。從它的收藏中,研究人員能找到對抗健康殺手的潛力股。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栗豆樹(Moreton Bay chestnut ﹝Castanospermum australe﹞),它是澳洲的原生樹種,種子內含有栗樹精(castanospermine),可以抑制一些特殊酵素,包含病毒複製過程中所需要的酵素,因此它也被廣泛地用來治療愛滋病。

面對當地人民與專家學者的權利,皇家植物園一直小心翼翼地拿捏雙方的平衡。皇家植物園與約一百個國家的在地社區進行合作,這些地區仍舊相當倚重傳統藥草的醫療方式。西蒙茲說:「這是個雙贏的局面。這些藥草會是未來最有可能發展成新藥的希望;且若當地的植物被開發成新藥,當地社區也會因此獲益。然而我們也不能只專注在藥物發展這一件事上,還必須同時兼顧對當地社區的尊重,並協助保育他們的自然資產。」
在某些特定地區,比如漠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大部分人民、尤其是住在鄉村更為貧窮的居民,對傳統藥草的倚重,更甚於來自「大藥廠」的藥物。西蒙茲承認:「相較於現代藥物,有些地區的人們似乎更相信傳統草藥。進一步了解這背後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現代醫療中,一些商品化的藥物對人們幫助很大;尤其是疫苗的施打,如果他們拒絕,就很可能遭受非必要的死亡。」
保存當地傳統藥草的知識,與保存藥用植物本身同樣重要。舉例來說,在迦納(Ghana)的某些社區,對傳統藥草的認知有著很大的落差。在二十八歲到五十七歲的年齡層中,仍有相當比例的人知悉這些藥草醫療知識;可是在十八歲到二十七歲的年齡層中,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知道這些知識。「越來越少年輕人會注意到傳統草藥,特別是住在城市裡的人,」西蒙茲說。「相反地,有些村落還留有一些耆老,保有辨識高品質藥用植物的專業智慧。」
假如我們能從傳統藥草研究中獲益,那麼一定要確保在全新的、透明的策略下,這些利益能夠共享。當地的人們必須享有利益,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守護著這些有醫療效用的植物;研究人員也得享有利益,因為他們讓人們更進一步瞭解植物如何能做為藥物使用;還有藥廠,藥廠在前兩者的引領下投資新藥的開發,使人們有安全的藥物可用。
第17章
生物多樣性大揭密
UNLOCKING BIODIVERSITY
在皇家植物園標本館一樓,沁涼的圖書館牆上裝設了一排窗戶,讓訪客得以一窺受嚴密溫濕調控的諾大貯存室裡保存的大量稀有藏書。這些藏書是圖書館最珍貴的一些皮革裝訂書籍,有些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後期。牛津植物學家約翰‧希索普(John Sibthorp)和著名的奧地利植物插畫家費迪南德‧鮑爾(Ferdinand Bauer)在一八○六到一八四○年間出版的十卷分裝《希臘植物誌》(Flora Graeca)也在其中。兩人於一七八六到八七年的兩年間,在東地中海航行從事學術考察,但之後卻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整理、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由於技術上和財務上的困難,當時只能限量出版六十五套。然而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這部書在當時被認為是植物學的空前鉅作,在市場上取得很好的銷售成績。精緻的書頁令人愛不釋手,優美的版畫更成功捕捉了他們所發現的每一個物種。
雖然這些植物誌製作非常精美,有著漂亮的手繪全頁插圖,但真正重要之處不在於這些金錢或歷史上的價值,而是它們所記錄的生物多樣性。這些植物誌是我們開始描述特定區域裡所有物種的最初成果,也成為我們對待地球資產的態度轉捩點。它們也是我們評斷已知物種在特定地點存活或消亡的基礎。儘管這些書卷一開始是為上流社會人士所出版,用來在同儕間炫耀這些從全球收集來的知識,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這些地區性的植物誌成為科學上最實用的紀錄工具。
時至今日,製作植物誌仍是皇家植物園的基礎工作之一。「植物誌」一詞是指生長在某一地理區域裡,所有野生植物物種(有時也包括外來種和入侵種)的紀錄。目的是讓讀者能夠辦認出這些物種。雖然植物誌原文為「Flora」,但內容通常也包括了針葉樹、蘚苔和蕨類等非開花植物。
在過去,植物誌都是裝訂成卷,包括便於攜帶至田野地辨識植物的小開本「田野植物誌」(Field floras),以及適合在家仔細研讀的大部精裝詳盡植物誌。如今考量經濟效益和實用性,許多現代植物誌都已上傳網路或製成電子書,讓無法親自造訪植物學圖書館的讀者們也能使用;同時也能在小型的手持設備上開啟,方便在田野地隨時查找資料。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論文〈談真菌孢子的萌芽〉被「放在桌上」,就是林奈學會中所說的「被接受但沒經過公開討論」階段。此段文章摘錄於
《Beatrix Potter: A Life in Nature 波特小姐和彼得兔的故事》一書。
* 松塔牛肝菌(學名Strobilomyces strobilaceus),1893年9月3日畫於Eastwood。碧雅翠絲在這張圖背面畫了一張地圖,像麥金多斯指出她是在哪裡發現及畫下這種稀有的真菌。(蘇格蘭柏斯博物館及藝術畫廊慨允借用)
* 毛地黃(Digitalis purpurea)
* 烏頭(Aconitum napellus),是莎士比亞劇作裡家喻戶曉的角色──羅密歐用來自殺的毒藥。
──延伸閱讀《Beatrix Potter: A Life in Nature 波特小姐和彼得兔的故事》
── 內容摘錄自《 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一書;除非另行註明,書中所有圖片的版權皆屬英國皇家植物園信託委員會所有;分享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