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皇家
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 (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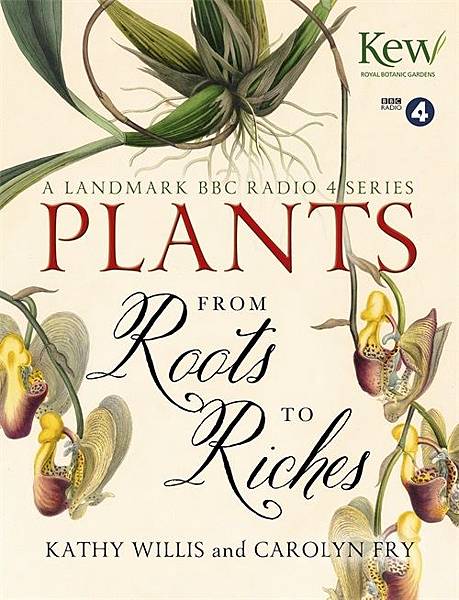
第3章
植物標本的無限可能
PRESSED PLANTS AND POSSIBILITIES

皇家植物園一間玻璃隔間的會議室裡,一群植物學家熱切地檢查一疊奈及利亞的太陽報。他們對頁面上微笑的非洲時尚達人不感興趣,反倒專注於那些躺在摺疊的報紙間、有著壓平了的枝條、樹葉和花朵的乾燥標本。皇家植物園潮濕熱帶團隊(非洲)的分類學家們,與英國及當地同仁們一起,在奈及利亞的加沙卡古姆蒂國家公園(Gashaka Gumti National Park)採集了這些標本,並帶回倫敦西部。這些標本中可能包含稀有或未知的物種,也可能包含能製成重要藥物的植物,但在它們被正確辨識出來之前,沒有人知道結果。要瞭解更多關於此公園的植物相,這件工作非常急迫,因為它的森林已經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今天的會議要把標本分別歸類到各自所屬的科別內,這是解開其奧秘的第一步。這項工作完成後,各種植物會被分別交付給相關的分類學家鑑定屬別和種別,貼到無酸紙上後歸檔,進入科學上的正確位置──由皇家植物園七百五十萬份標本所構成、巨大乾燥植物的「家族樹」中。

植物標本館是保存標本的所在。這批標本已經壓平、乾燥、並貼在紙上,或保存於充滿酒精的玻璃瓶中。植物標本館的存在,正是植物園與其它類型園林最大的不同點。
最早的植物標本館被稱為「乾燥花園 (horti sicci)」,源於十六世紀義大利的新藥用植物園,由上面貼有乾燥植物的紙張裝訂成冊,集結而成。漢斯‧斯隆 (Hans Sloane)於一七五三年捐贈給大英博物館的壯觀植物標本收藏品,也是採用這種保存方法。然而,十八世紀出現了許多新物種──眾多探險旅程所造成的結果──而且有了新的林奈氏分類法,使用散裝紙張變得比較方便;當有新品種或新分類規則出現時,可以隨時加入紀錄。約瑟夫‧班克斯的植物標本館就是採用此形式。
植物標本館與圖書館或博物館不同的特色之一是:一間管理完善的植物標本館,標本存放的位置會不時更動,以符合對植物親緣關係最新的詮釋。一間靜止的植物標本館,只能算是收藏死去植物的博物館;真正的植物標本館,是個活生生的研究工具。

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是全世界最大的標本館之一,每張臺紙上只展示一個物種的單一標本。同一屬(科以下的分類層級)的物種被歸檔在同一檔案夾裡;接著,同科不同屬的各個檔案夾,會被一起放進這個科別專用的檔案櫃裡。而皇家植物園的分類學家,則利用他們對全球植物多樣性的專業知識,確保每一個物種都能和它們的近親一起被歸檔在正確位置。如此一來,想要瞭解某種特定植物屬性的科學家們,就能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相關標本。館內的標本來自世界各地,由各式各樣的人們在過去數百年間陸續收集而來,形成一間皇家植物園工作用的重要參考圖書館。植物標本館館長大衛‧辛普森 (Dave Simpson)即表示:「我們最古老的標本可以追溯到西元一七○○年,但大多數的標本都來自十九世紀中葉。」

皇家植物園裡的古老標本,例如班克斯的那些植物標本,與現代標本的主要差異在於標籤品質的不同。現代的標籤上充滿了各種資訊,包括此植物的採集位置及其周遭的生態環境。標籤上也會包含此樣本無法明顯提供的植物細節,例如樹高或花朵原本的顏色;相反地,一份古老標本的標籤上,如果有任何紀錄,可能也只標示了採集的年分或國家。
皇家植物園植物標本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八四○年、植物園的所有權由皇室轉移到政府之時。到了一八三○年代,歸功於班克斯,許多英國殖民地都已成立植物園,但他們的成立原因卻各有不同。有些是出於當地首長對植物學的熱情,有些植物園的成立卻僅僅是為了替罪犯提供工作。一八三八年,約翰‧林德利 (John Lindley)──倫敦大學學院的植物學教授,也是倫敦園藝學會的助理秘書──寫了一份關於不同皇家園林的報告給政府,這些園林在喬治三世與班克斯於一八二○年雙雙過世之後不斷沒落。為了節省預算,英國財政部還曾質疑這些皇室園林是否真有存在的需要。

然而,林德利沒有接受關閉植物園的意見,反而提出要將皇室贊助的皇家植物園改為由政府預算補助,「以促進整個帝國的植物科學。」他相信,如果由皇家植物園統一管理,大英帝國海外的雜牌軍植物園應可為醫藥、商業、農業和園藝帶來莫大助益:「它們都應該受植物園園長的掌控,與他同步作業,透過他彼此合作,持續向母園回報工作進度、說明所需並接收物資,然後利用植物界中所有有用的一切,來幫助祖國。」
為了要調查不同植物資源所蘊含的商業財富,政府需要皇家植物園來找出哪些植物可能具有商機、而它們又生長在哪裡。林德利曾在班克斯的倫敦宅邸中工作過,利用班克斯的收藏品來進行玫瑰的分類,他在這份報告中要求建立「一個龐大的植物標本館及藏書可觀的圖書館」,以協助鑑定和命名植物。政府派來將皇家植物園發展成國家植物園的人選威廉‧傑克遜‧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以非常認真的態度看待林德利的報告。胡克是位敏銳的植物收藏家暨分類學者,年僅二十歲便已鑑定出他第一個尚未為英國所知的新品種── 無葉煙桿蘚(Buxbaumia aphylla)。當一八四一年出任皇家植物園園長時,他帶來了自己的標本館和圖書館,並占用了住所「西園(West Park)」好幾個房間。他對自己的目標極富野心:「我下定決心,將不惜任何代價,盡力讓我的植物標本館成為歐洲的私人收藏中最豐富的一個。」

隨著時間過去,胡克鼓勵其他植物學家和機構出讓收藏品,以成立皇家植物園所屬一個單獨的植物標本館。一八五二年,植物學家暨旅行家威廉‧伯姆菲爾德(William Bromfeld)收藏的植物標本率先被正式收購;兩年後,植物學家喬治‧邊沁(George Bentham)用鐵路送來了四大貨櫃的標本;然後在一八五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捐贈了幾批數量龐大、但有部分受到害蟲或濕氣破壞的植物標本。
有許多來到皇家植物園的植物標本,是個別植物學家寄給胡克的。在十九世紀初期,薪水很低的兼職博物學家與富裕的獨立研究者間彼此通信,是很平常的現象。兼職學者往往無法負擔昂貴的自然史專書,也無法進入相關的博物館,但兩者卻都是從事標本分類所必需的;因此,他們試圖和能取得這些資源的「仕紳」收藏家們建立友好關係。藉著這種方式,兼職學者以他們在居住地所採集的樣本,換取與他們所選擇科目有關的知識。而在與這些紳仕收藏家較勁、切磋相關知識和技能的過程中,這些學者也可獲得一定的地位。
在胡克的一生中,他熱衷於和別人分享發現新事物的快感,並鼓勵許多植物學家和他通信。為了追求科學真理,他跨越了嚴格的社會鴻溝,許多被他提到的蒐集者都是勞工階層的工匠,往往投身於研究像他們自身一樣被社會所忽略的微小植物,例如苔蘚和地衣。這些滿懷熱忱的植物達人仔細搜查他們居住的地區,尋找不尋常的植物,然後在無法確認某種特定標本時,謙恭地諮詢胡克的意見。威廉‧班特利(William Bentley),曼徹斯特附近羅伊頓(Royton)的一個鐵匠,戰戰競競地這麼寫道:「懷著微渺的信心,我藉這封信試圖接近您......在植物學的浩瀚領域中,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工人們沒有任何人可以追隨,﹝所以﹞我們把您當作是科學上的父親,必會將所有的困難都擺在您面前。」

胡克的通信網遠遠延伸到故鄉之外。一些熱心的博物學家從澳洲附近的範迪門地(Van Diemen's Land,現在的塔斯馬尼亞)寫信給他,當時此地已被英國殖民,並在一八○三年成立流放殖民地。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島上鬱鬱蔥蔥的溫帶雨林出產了豐富的新植物標本。流放罪犯管理員暨多產的植物採集者羅納德‧坎貝爾‧昆恩(Ronald Campbell Gunn),在一封寫於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寄給胡克的信上,坦承自己在辨別及命名植物上的困難:
我現在越來越急著想要認識那些常見植物之外、新的或尚未被描述過的植物──它將使我在採集植物時知所取捨,而且有很多屬別我甚至還不熟悉。巴克豪斯﹝詹姆斯‧巴克豪斯(James Backhouse),一位曾拜訪澳大利亞罪犯殖民地的博物學家﹞常說「就算幫植物取錯名字也好過沒有名字」,但我並不傾向於遵循這個原則,因為我覺得一旦幫植物取了錯誤的名字,這些名字往往會執拗地流傳下去──而沒有名字的植物們,早已準備好要被正確地命名。

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六○年之間,昆恩寄給了胡克數百個標本,要求交換能幫助自己增進知識的參考書:「你寄來的各種領域的書總是不會錯的──植物醫學,以及等等之類的。我所擁有的植物學知識,讓我對後者那類書甚有興趣。」
多年來,隨著胡克的忠實通信者寄來成箱成箱的標本,他的植物標本館不斷壯大。一八五三年,這批收藏隨著胡克從「西園」搬進了「獵人之家(Hunter House)」,這是泰晤士河畔的一幢獨棟房屋,以前是漢諾威國王的舊居。一八六五年胡克去世後,政府以一千英鎊的代價買下了他私人的植物標本收藏,併入皇家植物園的收藏當中。一八七七年,「獵人之家」加建新的側翼以容納這些收藏,但空間仍然是個問題;正如一八九九年,皇家植物園園長威廉‧西塞爾頓‧戴爾(William Thiselton-Dyer)對工程處(Office of Works)所解釋的:「我無法控制皇家植物園標本館的擴張,因為我無法控制帝國的擴張。新領域的科學研究,是隨著帝國版圖擴張而增長的。」一九○二年至一九六八年間「獵人之家」已經又增建了三翼,並在一九八八年進一步擴建為方庭(quadrangle)。

二○○七年,隨著標本仍以每年三萬五千件到五萬件的速度持續湧入,皇家植物園委託愛德華‧考利南建築師事務所(Eaward Cullinan Architects)興建一座占地五千平方公尺、附有氣候控制系統的新建築,以容納圖書館和部分的標本館。此設計旨在防範洪水和蟲害,在未來五十年內應可為植物標本們提供足夠的收藏空間。
如今,植物園有著嚴格的規範,規定新來的標本該如何從新大樓兼具木質與玻璃結構的弧形大廳,抵達標本館龐大植物檔案系統中的正確位置。一開始它們被儲存在特製的黑色架上,所有內含植物材料的包裹都從大廳右轉,通過雙層門進入皇家植物園的「汙染區」。在這裡,有三天時間它們被冷凍在攝氏零下四十度低溫的大型步入式冷凍庫中,以殺死任何能啃食植物的害蟲,像是窄斑皮蠹(Trogoderma angustum)這種甲蟲和它們的卵。之後,這些標本才能被帶進相鄰的標本管理組(Collections Management Unit,CMU)內打開。新進的每一個樣本都會被標上一個獨特的號碼,以此追蹤樣本在標本館內的行進路徑。彩色標籤標記了這些包裹是剛被歸還、亦或即將出借的標本;是等待寄出的禮物、還是需要進行鑑定並收藏於標本館中的新樣本。
初來乍到的標本可能要花上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正確地在標本館中歸檔;但即便被歸入某個特定的檔案夾,它們也可能不會在裡面待太久。隨著植物親緣關係的新資訊出現,標本在標本館中的位置也會隨著這些研究結果而更動。特別是DNA技術的最新發展,促進了標本館中的某些重大改組。一八六九年,標本館內的標本是根據威廉‧胡克的兒子約瑟夫和植物學家喬治‧邊沁所設計的分類系統來擺放。這個系統反映了當時對植物演化關係的觀點,比起林奈時代已有相當大的改變。近年來,歸功於分子特徵和DNA基因定序的研究,我們對植物親緣關係的知識也有了顯著的增長。
目前標本館的標本排列方式,根據的是一套新系統APG III(APG代表被子植物系統發育小組,這是一個植物學家的非正式網路,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形成,目的是使用DNA定序的結果,來產生被子植物或開花植物科別分類的新系統)。這種改變產生了一些令人吃驚的新關係。例如,當標本館檢查並鑑定生長在亞洲熱帶地區的新進植物標本時,發現大王花(Rafflesia)──它所開的花是世界所有植物當中最大的,直徑可達一公尺,聞起來像是腐爛的肉──和聖誕紅(Euphorbia pulcherrima)有親緣關係,然而聖誕紅卻是世界上花朵最小的植物之一。紅色的「花瓣」,實際上是圍繞著花的苞片。


只要繞著標本館走一圈,就可以清楚看見標本館多年來朝有機模式發展及轉變的成果。在這棟有著落地窗的新大樓內,現代分類學家所採用的高科技工具和技術均能採行。同時,標本館最古老的側翼,仍有著華麗的紅色螺旋梯、挑高天花板和實木嵌鑲地板,讓人想起大英帝國時期、那段世界上大部分植物群都還不為人知的時光。
個別的植物標本,同樣反映了皇家植物園的悠久歷史。在標本館的某個檔案夾中有著多年生禾本科植物小舌早熟禾(Poaligularis)的三株乾燥稻莖,其中至少有一株是一八三一年至三六年間達爾文隨小獵犬號遠航巴塔哥尼亞(Patagonia)時採集的。這些植物玉米色的糾結葉片牢牢地黏在臺紙上,莖的上端有著完整稻穗。達爾文在這張標本上手寫了註釋,標記採集位置:「巴塔哥尼亞海岸,布蘭卡港(Bahia Blanca),一八三二年十月初,C.Darwin。」這份標本貼在威廉‧胡克標本館的招牌藍色臺紙上,上面印有「一八六七年胡克植物標本館(Herbarium Hookerianum)」,那是這些標本正式納入標本館館藏的時間。
後來加註上去的還有皇家植物園的條碼,這顯示此標本已被數位化,以便植物學家從全世界任何角落連線查詢。如同標本館助理館長比爾‧貝克(Bill Baker)所解釋的:「達爾文的原始標本還是非常有用的;你仍然可以剝離下一朵小花並將其煮沸﹝補充水分以供查驗﹞。重要的是,不要把這些乾燥植物僅僅視為是歷史文物。這是皇家植物園三十五萬份『模式標本』﹝描述新物種時所依據的原始標本﹞中的一份。『模式標本』永久的模式化、並固定了物種的名稱。雖然在科學上不一定重要,模式標本卻是我們用來組織並管理植物命名的方法。」

出於對秩序和層級結構的熱愛,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在一百五十年前開始建立皇家植物園的標本館。對他們來說,世界是透過一個神聖系統,來區分為貴族、商人與勞工階級;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基督徒及異教徒。他們認為植物也有著相同的秩序,而植物標本館被視為是這種層級結構的具體表現。
隨著這些年新樣本不斷加入,標本館已經發展到遠超過那些精心歸檔的部分。它的組織師法植物的親緣關係,讓植物學家得以歸納出植物間的關聯性;也只有在此處才能被發現的關聯性。舉個例子來說,一九八○年代末期,科學家們正在尋找用來治療愛滋病的新型抗病毒藥物。他們在栗豆(Castanospermum australe,別名澳洲栗)中發現了一種很有希望的化學物質;這是一種澳洲東部特有的樹木,但是族群相當稀少。當科學家向皇家植物園詢問這種樹有沒有哪個近親,可能拿來生產相同或類似的藥物時,植物園的分類學家指出有一種更容易取得的南美洲物種,其含有完全相同的化學物質。如果沒有標本館的資源,很可能根本不會有人想到要往南美洲找。

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時,標本館也非常有用,因為每個樣本上都有一些關於植物本身和採集地點的植物學資訊。在現代標本中,這些資訊包括了用全球定位系統收集來的、高度準確的位置數據。隨著氣候變化影響植物的生命週期,這組數據對於辨別植物棲地分布的變化來說非常寶貴。正如貝克所解釋:「最關鍵的一點是,標本館記錄了哪些植物曾經出現在哪裡,讓我們得以看出它們的分布是否隨著時間發生變化,或因棲地的破壞而縮小。如此,我們得以量化物種面臨滅絕的危險性。」
回到那個試著將標本歸入不同科別的會議裡,潮濕熱帶團隊(非洲)的負責人馬丁‧齊克(Martin Cheek)有條不紊地工作,試著辨別一株莖部有卷鬚纏繞的乾燥標本。這項特徵顯示,此植物只可能來自下列三科:葫蘆科(瓜類)、葡萄科、或是西番蓮科。查看卷鬚所在位置的細節及果實後,他判斷這株植物應該屬於葫蘆科。這種耗時的工作需要相當多的經驗,是保育非洲多樣植物相的關鍵。一九九五年至二○○三年間,在鄰近的喀麥隆所進行的類似採集取得了兩千四百四十種植物,其中有十分之一對科學界來說是新品種。
這些標本,加上館內那些可以追溯到胡克時代的標本,讓皇家植物園的科學家們得以辨識下述物種:根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所制定的評估標準,在這兩千四百四十種植物當中,有八百一十五種是受威脅物種」。皇家植物園的地圖顯示,含有高密度瀕危物種的區域與現有的國家公園區域並不相符,因為原本的國家公園不是為植物、而是為動物所設立的。因此,喀麥隆政府另外成立了占地二萬九千三百二十公頃的巴克斯國家公園(Bakossi National Park),以保護這個新發現的生物多樣性熱點。正如齊克所解釋的:「在我們開始這些工作之前,喀麥隆的這個地區根本不在任何保育地圖上;但在我們完成工作的時候,這個區域已經成為熱帶非洲地區數一數二的植物多樣性中心。」
誕生於維多利亞時期蒐集熱潮的皇家植物園標本館,如今已成為保育世界植物相的一項重要工具。
*查爾斯‧達爾文採集的小舌早熟禾植物標本,上頭有他的簽名
* 威廉‧傑克遜‧胡克 (William Jackson Hooker )是皇家植物園首任園長
── 內容摘錄自《 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 PLANTS FROM ROOTS TO RICHES》一書;除非另行註明,書中所有圖片的版權皆屬英國皇家植物園信託委員會所有;分享請註明出處。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